科學史是科學與人文交叉會通的高端新型前沿學科,也是滲透文理、貫通古今、融匯中西的典型橋梁學科。
科學史學科的誕生本身就有著強烈地彌合兩種文化(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)的學術動機和學理機制。如科學史學科之父喬治·薩頓所言,日益分離和隔絕的科學學科與人文學科將造成人類文化的分裂,為了防止這種分裂,必須在它們之間架設橋梁,而科學史就是這樣的橋梁學科。
上周應邀參加第七屆中國科技政策論壇,其中有一個“科學普及與教育”的專題對話。此一環節開始之前,我做了一個有關科學閱讀的簡要報告,提出在學校科學課程之外開展的科學閱讀,也是培養學生科學興趣并提升其科學素養的一條有效途徑。遺憾的是,眼下這方面的閱讀還不太受重視,許多人以為有了科學課,孩子與科學的“接觸”就夠了。
在對話環節,好幾位聽眾的提問,都涉及包括科學閱讀在內的科學教育話題。我以科學史上含鉛汽油與殺蟲劑的應用為例,舉證了聽眾所問科學普及對科技政策帶來的影響。這實際上也是考慮科學對社會的影響時非常典型的“案例”。現如今,諸如干細胞、基因編輯、核能、轉基因、全球變暖、疫苗等等社會性科學議題,一直都是社會論辯的焦點。我們的科學普及和科學教育,都不可能規避,尤其是它們所牽扯的社會倫理問題。
我也專門談到美國科學促進會對于一項開創性課程的總結:科學課程應當將科學安置在歷史的視角上。接受通識教育的學生(無論主修專業是不是科學)都應當將科學看作是知識、社會與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來修完科學課程。科學課程也必須通過強調它在倫理、社會、經濟和政治維度上的價值來傳遞上述內容。
特別是,將科學史引入科學課堂中,具有非凡的意義。美國在1985年啟動的《2061計劃》的一個特色,就是在學校科學教學中給予科學史一席之地,其第10章在介紹“歷史視角”時指出:“這里強調的是可以代表科學知識的演化與影響的10個重大發現與變革:地球是行星、萬有引力、相對論、地質時期、板塊構造理論、物質守恒、放射現象與核裂變、物種進化、疾病的本質和工業革命。”正是歷史上這些科學嘗試的片段,形成了我們的文化傳承。
我想借題發揮的一個觀點是,我們的科學普及或科學閱讀,也不能忽略科學史寬闊的視野。回望自己走進科學世界和愛上科學寫作的歷程,頗有些感觸——這恰恰跟我少時與科學史的接觸大有關聯。
記得是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,我向老師提出了一個問題:“為什么把平角定為180度,而不是100度或200度?”老師對我說:這是早就定下來的數學規則。這個回答并不能讓我滿意。后來,我從一本科普書上讀到:古巴比倫人崇拜太陽,他們看到太陽每天東升西落,在天空中走過一個半圓弧。比畫起來,這半圓弧的弧長正好相當于180個太陽視大小的累加,于是他們就把平角定為180度,而整圓就是360度了。原來如此!我既驚訝又興奮,仿佛自己在科學上也有了一個新發現,由此愛上了數學。
幾年過后,我偶然讀到一本科學隨筆集《阿西莫夫論化學》,旋即就被該書那通俗易懂而又妙趣橫生的獨特文體所迷住。該書第一章“稱重游戲”,講的是原子量概念的形成和測定,卻一點也不顯得枯燥,貫穿其間的是一條科學的思想方法的主線;第二章“緩慢的燃燒”,則以輕松、調侃的筆調,講述了氫、氧的發現歷程與燃燒的本質,還評論了幾位科學家的品德和人格。這個薄薄的科普小冊子成了我的化學啟蒙讀物,它向我昭示:科學發現的歷程盡管充滿艱辛,但也不乏樂趣。喜歡上它,是我真正熱愛學習并學會思考的開始,阿西莫夫由此也成了我的科學偶像。或許那也正是我喜歡科學寫作,尤其是創作科學隨筆的淵源。
2017年5月,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宣告成立。我采訪該系創系主任吳國盛教授時,聽他對科學史做了一個十分精辟的概括:科學史是科學與人文交叉會通的高端新型前沿學科,也是滲透文理、貫通古今、融匯中西的典型橋梁學科。他還談到,學習科學史可以增加自然科學教學的趣味性,有助于理科教學,也有助于理解科學的批判性和統一性,理解科學的社會角色和人文意義。
是啊,今天,科學對人類的命運影響是如此之大,而我們對科學的本質也許還缺乏認識。誠如吳國盛所言,過分地把科學工具化、實用化,帶來了許多問題。我們正處在科學發展的轉折點上,未來的科學指向何方?回顧科學的歷史也許能使我們有所省悟。正在成長著的一代年輕人,將主宰著未來的社會發展,如果一開始他們通過熟悉科學的歷史而全面的理解科學,那么科學就能更好地為人類造福。
在科學普及和科學教育中,都應該有科學史的一席之地。
XuYiedu.cn聲明:此消息系轉載網絡,XuYiedu.cn(盱眙教育網)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,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,不代表XuYiedu.cn立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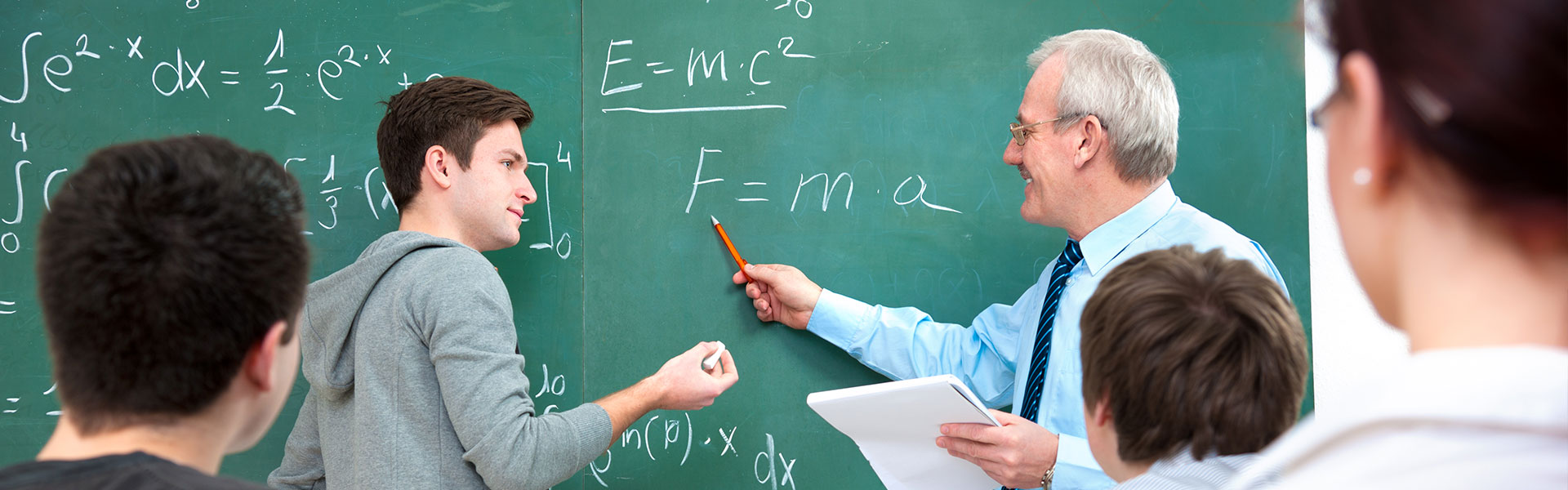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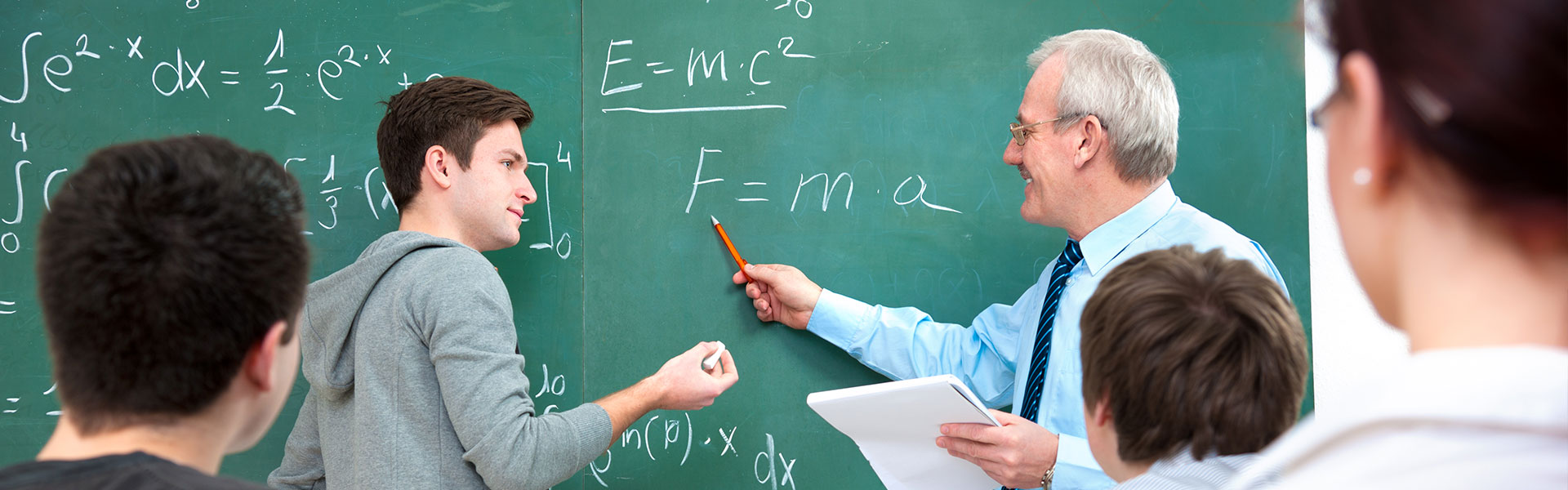


 2020亚洲欧美日韩在线观看
2020亚洲欧美日韩在线观看